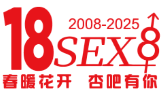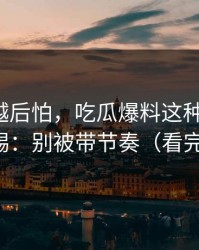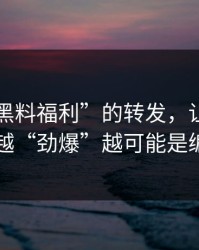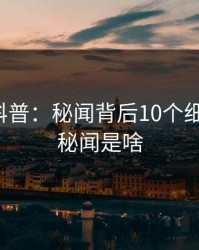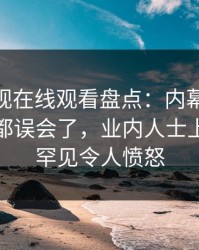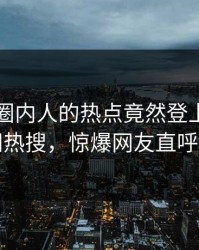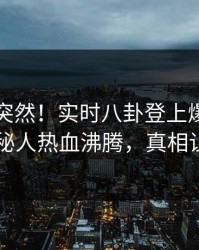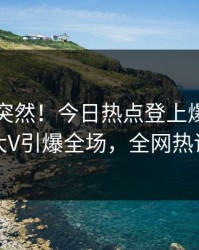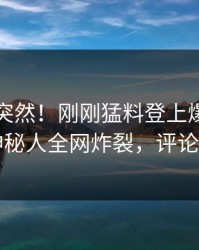【历史缝隙中的缄默群像】
公元986年,杨业殉国的消息传回汴京,杨府一夜之间挂满白幡。史书《宋史》用"杨业死,其子延昭继之"八个字轻描淡写地带过了这个家族最惨痛的转折,却只字未提那些突然沦为寡妇的女人们如何在血泪中重整旗鼓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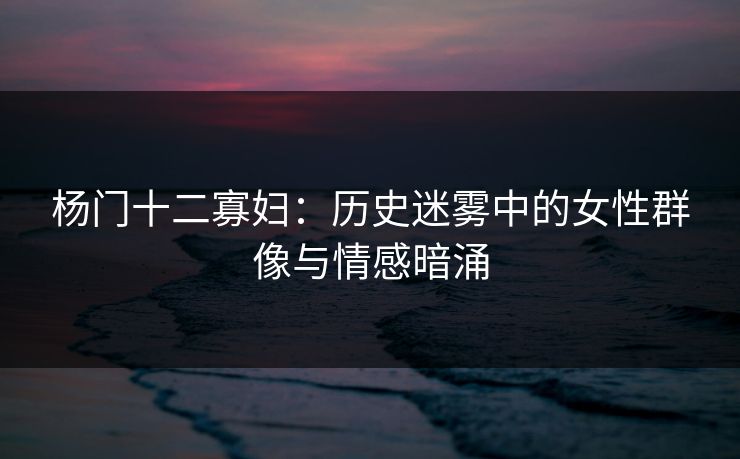
当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,会发现杨门十二寡妇并非文学虚构——根据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记载,杨业七子中确有六人战死沙场,加上姻亲关系的女性,形成一个规模惊人的寡妇群体。这些女性大多出身将门,如柴郡主本为后周皇室后裔,杜金娥原是山寨女杰,她们在失去丈夫后面临的是三重困境:国家需要她们延续杨家忠烈之名,宗族要求她们守节明志,而战场遗孤更需要她们独自抚养成人。
值得注意的是,北宋时期对寡妇再嫁的态度相对开明,《宋刑统》明确规定"夫亡……愿再嫁者听",范仲淹甚至为族中寡妇设立义庄资助再婚。但杨门寡妇却选择集体守节,这背后既有对杨家"忠烈传家"传统的维护,也可能暗含着对战争创伤的集体回避——每当夜幕降临,那些空置的婚床成为战争残酷性的沉默见证。
考古发现或许能给我们更多线索:1980年代山西代县杨忠武祠遗址出土的女性居所显示,寡妇院落设有独立的织机房、练兵场和佛堂,这种空间布局暗示着她们通过劳动、习武和信仰来应对情感创伤。其中一间卧房遗址的梳妆台下,曾发掘出保存完好的铜镜和玉梳,这些私人物件无声诉说着主人在肃穆守节外表下,依然保持的对美的渴望与对往昔温存的追忆。
【情感压抑下的暗涌与升华】
在礼教规范与情感需求的拉扯中,杨门寡妇们发展出独特的情感代偿机制。根据《杨家府演义》的描写,余太君每月朔望召集众人"演武堂前比试弓箭",这种集体活动不仅维持了军事技能,更创造了情感宣泄的出口。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,高强度体能训练能有效缓解创伤后应激障碍,这或许解释了为何杨家女将能保持惊人的战斗力。
民间传说中充满暧昧色彩的"穆桂英挂帅"故事,实则反映了人们对这些寡妇情感生活的隐秘想象。现存最早的元代杂剧《杨氏女挂帅》中,穆桂英与杨宗保的婚前恋情被大胆描写,其中"夜探营帐"的桥段虽经明清版本删改,仍保留着"红烛摇影,甲胄轻解"的含蓄暗示。
这些文学创作与其说是香艳描写,不如说是对战争寡妇情感权利的一种变相肯定。
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女性在极度压抑环境下展现的生命力。据地方志记载,杨门寡妇晚年多成为地方慈善领袖,捐建学堂、修桥铺路者甚众。杨琪之妻慕容氏守寡四十年后,创办的"忠烈绣坊"不仅传授纺织技艺,更收容战乱流离的妇女,形成北宋罕见的女性互助组织。这种将个人情感创伤转化为社会关怀的行为,体现了中国女性特有的韧性智慧。
当我们重新审视"杨门十二寡妇"这个题材时,应该超越猎奇视角,看到其中蕴含的深刻人文价值——在礼教与人性、忠义与私情、创伤与重生之间,这些女性用一生的实践书写了关于尊严与爱的复杂叙事。她们的故事提醒我们:历史不仅是男人的征伐史,更是无数女性在困境中寻找光明的心灵史。